杨奎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选择政治道路
11月25日,华东师大特聘教授杨奎松在复旦大学星空讲坛开讲,题目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讲座未开始,教室里便已挤满了人。杨教授先谈起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的中国游客“不文明”乱象,他提出:为什么有“中国人不文明”的说法,当下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该如何解释?是中西文化形态上的冲突,还是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冲突?
杨教授认为,今天大家看到的这种“不文明”的问题,绝不是亨廷顿讲的那种“文明”的冲突,而是不同社会发展程度所带来的人的观念意识习惯差异问题。所谓“不文明”形成的原因,简单说来,就是农业人口对城市公共生活方式的严重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从原先的百分之十几一路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急速扩张的城市化使大批农民成了市民,无论是适应国内城市生活方式,还是适应境外更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都需要时间。问题是,当下中国人多数还处于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过渡时期,多数人缺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公共意识,包括法治观念。
“因此,这样一种‘文明’的概念,更多的是指一个人的公共意识水平的问题。从传统的‘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小农生活方式,到遵守现代社会共同的规范、法律,养成在利他的基础上利己的观念意识,一个‘文明’的人和一个‘文明’的社会都要依赖于习惯的养成。而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代人很难实现,可能要两代、三代人,还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逐渐完善的法治的社会为基础。”
杨教授说,“不文明”乱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不仅西方社会同样有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以及各国原有的因种族、族群的历史隔阂而导致的发展差异,都使西方社会中一样存在着文明发展程度不同,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观念差异很大的情况。更不必说当今世界还有许多落后国家,还有很多人生活在部落社会中,或较原始的农牧业社会中,即使他们中一些人去西方留过学,有高等教育的文凭,他们往往还是会和工业社会中的人的观念意识格格不入。当今世界一概拿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达到的法律道德标准来衡量,甚至来要求所有国家、所有人,就更是容易弄出乱子来了。
理想受限于现实
杨教授研究的是中共党史,所以会谈到诸如社会发展程度问题、知识分子观念差异问题等,这是他研究探讨各色人等在1949年中国政治重大变革关头的不同选择问题时衍生出来的一些思考。在《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加写的“余论”中,他特别从理论的层面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
杨奎松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杨教授相信“存在决定意识”。他提出,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其思想观念总是要受到他所处时代及其条件的局限和左右的。从柏拉图到卢梭,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时代的烙印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无不历历可见。但是,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以国民的政治认同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普遍化。自十七八世纪欧美新型国家陆续形成后,世界各民族、各族群全部重新洗牌,先后进入到一个新建和重建国家的过程。古代那种“部分为整体而存在”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也逐渐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种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
现代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以相互平等的国民个人的共同认同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共同体。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古代中国开始迈入现代社会之门,必须重建国家之际,绝大多数国人实际上还处于封闭的农业社会的生存条件之中。而摆在少数能够接触到西方启蒙思想的知识人面前的,则是国际间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和国人在国际上被人看不起的严酷现实。
何谓知识分子?一个形象的说法称他们为“社会的良心”。所谓“社会的良心”,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生存的条件,一定是现代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知识分子不能犬儒”。换言之,现代知识分子理当有马克思那样的胸怀:把研究、思考和探讨人的平等、解放问题,当成自己的志业,亦即首先要有人权、人本、人性的意识,要站在关爱人的基础上来寻找人类解放的方法和道路。
但是,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却由不得他们走欧美知识分子那样先启蒙,再建国的道路。如果说英、美、法等现代国家的形成,都多少经历了一个众多国民自我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程序却不能不反过来。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都成了“爱国”第一,“爱人”其次的政治主张者。
杨教授举了几个例子:
严复
严复,中国最早的西方启蒙思想的译介者,他自1895年后即十分积极地译介西方的人权、自由、法制思想,反对君主专制。然而,1905年以后,他却转趋保守,重新认定中国非“专制”不可救。
比严复转得更快的是梁启超。梁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比严复晚,戊戌变法受挫之后赴日本避祸期间才开始较系统地接受并大力宣传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然而,1903年游美之后,他就迅速回归保守立场,开始主张中国必须实行“开明专制”了。
毛泽东,1919年开始涉足政治,起初也是跟着主张改良的胡适走,相信社会改造要一点一滴,从个人的修身养性做起,坚决反对暴力的流血革命。一年之后,和平改良尝试失败,他即转而接受了陈独秀、蔡和森等宣传的俄国革命的观点,开始主张阶级革命,相信非用暴力和专政不能改造中国了。
同样有此变化的,还可以举出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独立评论》派。他们全都是英美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1933年前后却围绕着如何救国的问题发生了分化。其中丁文江、蒋廷黻等一干人,转而开始公开主张中国必须实行“新式独裁”。
《独立评论》
导致中国众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几度发生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切与忧虑。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中许多人宁可暂时牺牲个人的利益,并且认定这也应该是全体国民应做的选择。当然,既然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政治认同,因此,政治理念不同,知识分子们所爱的国也会有所不同。
比如,同为自由主义者,1949年胡适选择帮着蒋介石去维护“自由中国”;储安平选择留下来追随***建新中国;张君劢则既不留大陆,也不去台湾,为坚持他的理想,宁愿去作“白俄”。但是,他们无不自认为自己是爱国者。
为什么追随***?
新中国建国后,不仅储安平等留了下来,不少留学国外的知识人也都选择了回国。他们选择的理由基本上也是一个。
物理化学家傅鹰
比如物理化学家傅鹰和夫人1949年时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却毅然于1950年10月回到大陆来帮助***建国。和今天讲得较多的在他之后回国的钱学森不同,傅鹰最初对***并不十分信任,一直到整风反右时,他还发表过不少批评***干部的言论。但是,就连毛泽东也认为他是衷心拥护***的,明确指示不能把他划为右派。为什么呢?
傅鹰在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期间不止一次地讲过,他对***有看法,但也很佩服***。因为,***让长期受屈辱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他说,让他最先开始看好***的,是1949年解放军渡长江的时候,竟然打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打了英国人,中共不仅不道歉,还接连发表言论痛斥英国政府,这让还在美国的他特别解气。回国后,正赶上中共出兵抗美援朝,看到解放军能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人赶过三八线,他更是觉得痛快。再加上看到中共刚建国就能调动几省力量去整治淮河、能够一鼓作气完成了许多国人空喊了几十年的土地改革,这都让他由衷地认同***。他说:我和***奔的是同一个门,都是为国家,***领路领得比我好,我当然跟他走。
根治淮河的历史
另一例子是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同样有好几年不喜欢***,但逐渐逐渐就变了。杨教授在讲座中举了顾颉刚1952年、1953年、1954年和1959年的四篇国庆日记,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思想转变的轨迹和主要原因:
1952年国庆日记(上海)
此次国庆节,将作终夜狂欢,局中同人有残弱者,闻之愁绝,盖秋夜甚凉,虑不胜也。又政府规定,多加游行之资产阶级须一律穿笔挺西装,系红领结,妇女须穿花花绿绿之旗袍,以有外国人参观,为表示国力富裕,故打破节约教训,迩来社会,行为虽整,心术愈诈,盖导之自上,实亦国家隐忧。既已切实建设,何必尽量作表面文章乎!
1953年国庆日记(上海)
今日所见游行队,与昔年所见异。一,……今皆无之。二,……今亦无之。此皆转变滑稽为严肃之征。
1954年国庆(北京)日记(上海)
今日八时半到天安门,二时退,实站立五小时半,膝头觉僵硬矣。忆廿年前,正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蓄意挑衅,在东长安街演习,汽车上大书一“战”字,日本妇女在林中送茶,予目击之,心痛甚,想到:“只要中国强,我死也甘心!”今日所见,中国竞强矣,为之大乐!此皆党之功也。
1959年国庆(北京)日记(上海)
今日为予首次进人民大会堂,其伟大崇高真匪夷所思,又首次用译音收听器(即麦克风),以发言者皆外宾也。此次国庆节,外国参加者八十三国,几包尽世界之国矣,盛大哉此阵容也!
1959年的人民大会堂
傅鹰、顾颉刚等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思想转变?杨教授以为大致有四个原因:
首先是***统一中国及强硬外交带来了民族自豪感;其次是***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猛进让人振奋;再次是***的阶级宣传和思想灌输使知识人产生了一种原罪感(相较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劳而获);最后是“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国家”的爱国宣传强化了他们的传统道德感。
由上不难看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很大程度上和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及环境的条件有关。虽然不少知识分子原来也曾经是欧美教育出来的,深具超党派、超民族、超国家的自由主义观念,但是,现实的国际环境和国人在国外的屈辱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大都成为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为先,“爱人”其次,这是理想受限于现实的一种结果。
当然,杨教授最后说明,这样的情况也并非只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究竟应该爱国在先,还是应该爱人在先,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至今困扰着许多国家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民族国家存在一天,这样的难题也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通货膨胀是贯穿于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也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关键要素。在国民政府人为制造却无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物价漫无限制的飞涨,使广大人民在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慌的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与希望。一个连其人民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政府,怎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且,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民政府的即将终结。以往学者们谈到过通货膨胀与国民政府覆亡的关系[1],但多数是就宏观与理论而言,对二者的具体过程则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通货膨胀下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这一切入点,细致地展现国民政府覆亡前的社会景象。
一、物价飞涨与生活困难
连续十多年的抗战与内战,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1945年9月为346,1946年12月为9713。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8倍。当时有人预言,“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2]。确实如其所言,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3](208-209)。1948年8月的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顾颉刚在日记中对金圆券贬值的过程进行了记述。仅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来说,在最初的时候,“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1949年1月18日,“一切物价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3月3日,“近日银圆二千七百元”。3月31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银圆与金圆券的比价,4月5日为二万八九千,10日六万,15日13万,16日18万,22日46-49万,27日130万,30日400万。到了5月19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翌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4](231,237-2381)。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物价的飞涨超乎了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带给他们犹如隔世的感觉。战前一封平信的邮价是5分钱,到1948年4月增长到五千元,还严重低于物价的指数。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算起来应该是一万六千五百元”。一枚五万元的邮票,连寄一封到国外去的航信都不够(后者至少十万元以上),却“约等于战前一个普通银行的基金”[5]。一口上好的棺木,战前不过四百元,战后却增长到200万元。带给老百姓的反差,是“能在十年前买大楼房二十所”[6]。然而,通货膨胀带给百姓的影响不仅仅是难以接受的感觉,还包括了他们具体生活的日益艰难。随着物价的飞涨,人民的收入虽有增长,但始终不能与物价同步,因而导致了他们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天津警察为例,当时报纸感叹,“警察一年来薪饷虽有增加,然而赶不上野马一般的物价。他们的生活委实太苦了”[7]。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飞涨不但造成了人们手中原有货币的贬值,更造成了收支方面的入不敷出。时人声称,通货膨胀对“靠薪水和工资吃饭的人最不利”[2]。
本文来自作者[夏侯林莹]投稿,不代表溟宇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gumingyu.com/zixun/202508-1903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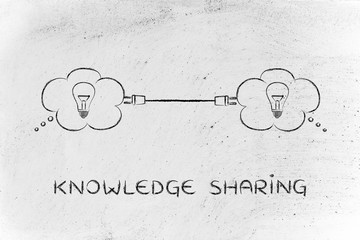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溟宇号的签约作者“夏侯林莹”
本文概览:杨奎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选择政治道路11月25日,华东师大特聘教授杨奎松在复旦大学星空讲坛开讲,题目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讲座未开始,教室里便已挤满了人...
文章不错《杨奎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选择政治道路》内容很有帮助